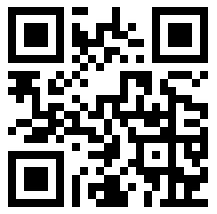-
»河北省周易研究会六届七次全体理事会顺12-01
-
»河北省周易研究会六届七次理事会会议纪12-01
-
»河北省周易研究会监事会召开会议09-25
-
»深刻领悟总书记讲话精神,认真做好当前09-25
-
»六届十二次常务(扩大)会议召开08-21
-
»石建和同志追悼会在石家庄殡仪馆举行07-17
-
»沉痛悼念石建和同志07-17
-
»众悼石会长07-16
-
»六届十一次常务(扩大)会召开06-13
-
»2025 国际易学大会第32届河北年04-14
-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万象幽玄,大道至11-13
-
»道学与量子物理的美好相遇(上篇)10-26
-
»道学与量子物理的美好相遇(下篇)10-26
-
»鬼谷子再下山正当时——浅议“以道驭术10-08
-
»中秋忆和仔09-24
-
»缅怀人文始祖,激励民族振兴——浅议09-22
-
»占以示学,义理优先——议王船山生平三09-20
-
»六十四卦所含信息浅析09-15
-
»重新认识《周易》经典文化价值09-15
-
»武当山金顶诸象蕴含的文化符号探微09-15
入神、存神、穷神:论张载的神化思想
《易传》中的“穷神知化”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宋之前的易学家都没有对神、化有系统的义理化诠释,王弼也是从玄学角度进行解释。到宋代,张载的《正蒙·神化篇》专门诠释了神、化及“穷神知化”的丰富含义,这对发展理学思想有重要意义,王船山就继承了张载的神化论,发展出“存神尽性”思想。张载的神化论与太虚、气的思想有重大关联。以往常常将太虚作为张载哲学的本体,但实际上神比太虚更具本体意义,牟宗三曾称之为“太虚神体”。同时,关于神化论中的入神、存神、穷神思想近几年研究较少。张岱年认为“存”即直觉,“存神”就是对神之直觉,但朱伯崑认为存神并非提倡直觉主义,因为它以入神为前提。但是,入神是发挥思虑以修养道德,而存神、穷神是不用智力的最高境界,有思有虑又如何能达到无修无为?本文结合前人研究,通过梳理入神、存神、穷神的修养过程,将穷神之境作为理性和直觉的结合,进一步讨论“与天为一”的气化境界。
一、神化论:最“本体”的本体论
(一)神与化
张载多次讨论神化与气的关系,比如:“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神为体,化为用,贯通于气。在阴阳之气中,神可以说是对立中的统一性,化是统一中的对立性。神是化的不测之本体,化是神在阴阳二气中的渐进之作用,“化是对宇宙间氤氲不息的生灭过程的实然把握,而神则是其内在根据”。神是气化的源泉和动力因,化是气化的形式、过程、规律。张载说:“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神化是天道之功能,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张载解“神无方而易无体”为:“以其不测,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体。”神与易都统一为天道。生生之天道叫做易,没有形体;不测之天道叫做神,没有固定方位。易与化相接近,代表天道的生生变化,变动不居。神具有普遍性,其大无外,贯通于人伦日用之中,如日月无所不照。神化是“大且一”,没有限制,故无方、无体。神“不疾而速”,推动神速之变化,故不可测度;化是精细隐微的变化,循序渐进于无形中,故难以知晓。《系辞》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统一万物之运动。阴阳二端相互感应的原因在于神和化,神是气运动的本性和根源,化是运动的规则和过程。因为人也是气化而成,故通晓气化之规律就能使生活变化日新。化之境界是不凝滞于外物,随天地之气汇合为一体,此为至诚之道,也是“大而化之”的圣人境界。能合乎天地的阴阳之德,与天地之气同流而无所不通。圣人以与天地之气同流为最高德行,安于气化,不留不滞,安时处顺,随圆就方,此即存神境界。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张载认为,存神过化能够让人泯除外物之牵累,顺应性命之安排,即“忘物累而顺性命”。顺应气化也表现为因时制宜,“天之化也运诸气,人之化也顺夫时”。气化在人事表现为时,生命活动顺应时势就是顺应宇宙运行之法则。张载说:“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措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神是礼义之根源,穷神表现为合乎时宜,合乎时宜表现为合乎礼义。穷神是让人顺应事物之变化,意识到世事皆是无常,从而不计较个人之得失,获得精神之解脱。
(二)神与太虚
关于太虚和神的关系,张载说:“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神是太虚运行的功能和气之聚散的推动力,是“太虚—气—万物”整个转化过程的动力之源,因为神的作用,太虚之气才活动起来,生生不息。因为神的存在,太虚之气才不至于僵化,太和才能生生不息地运动,使得宇宙万物变化无穷,“神化正是‘太和’之道的具体展现”。“鬼神”之“神”与“穷神”之“神”不同,鬼神代表气之散聚,神化是太和之道的运动功能。在张载那里,“神化论”比“太虚论”更具有本体意义。在《正蒙》中,神出现的次数是一百二十余次,比太虚和气出现的总和还要多。神是推动天地生生变化的神明、妙道,是万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因。神具有主体性、能动性,赋予万物生生不息的动力,是变化之道的根本:“唯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动。”翟奎凤认为:“神在化中,化为神用,两者又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神为一、化为两。”神是一,是气化过程中阴阳和合的统一性;化是二,是气化过程中阴阳相摩相荡的对立性。不是先有一再有二,而是一本身就包含着二,二的背后有一提供动力。神之作用通过化来展开,神、化相即不离。神在化中,因为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而无方无体,不可测度;化中有神,故化之推行变化最终统一于一。化是气化之功能,神是气化之本体。神比太虚的本体性更纯粹、更彻底。张载关于太虚的很多说法有着形而下的色彩,比如:“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是将太虚描述为有形之物消散而成的状态,是充满流动之气的虚空,这里的太虚有着最终极的质料的意义,“包括他(张载)有时也把‘太虚’说成‘虚空’,也带有一定经验性空间意味,可以说张载所说‘太虚’一定意义上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哲学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太虚有时具有一种经验性的空间意义,不具有本体意义,最具本体性的应该是神化。杨立华也说:“虚和气这‘两体’,其实都是贯通于气化过程始终的‘一物’的印痕和残迹。而这贯通‘两体’的“一物”,其实就是超越性的神化作用。”神和化的共同作用开显出太虚、气、万物三者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故神化论才是张载哲学中真正的本体论。
二、精义、入神、存神:通向穷神知化之路
(一)精义方能入神
《系辞下》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张载解释:“‘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穷神知化’,乃养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精义入神’,养之至也。”精义即精研义理,精一于义。精义是由内而外之修养路径,通过内在崇德、养性、存心,以达习惯成自然的纯熟状态,就入于神化,这是穷神一方面的表现。君子精一于践行仁义,久而久之到不思不勉、自然而成的境界,就能执一御万,彰往察来,见几而作。精义是穷神的必由之路。精义入神是内在养德,利用安身是外在求利,二者相辅相成。精义入神是养德至精益求精的境界,穷神知化是内外共同作用的自然无为、身心合一之境。张岱年将“内”与“外”解为心与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神化是道德和知识的互相结合,但这不如将前者解释为穷理尽性、存心养性之内修,后者为道德践履、发挥功用之外修,两者是知和行的统一,穷神知化是内修与外修互相促进的水到渠成的结果。
张载说:“‘知几其神’,‘精义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见事于未萌。豫,即神也。”豫是事物萌发之前的必要准备,“知几”即是豫,豫之道就是神之道。通过了解事物发展的苗头来知晓事物发展之动因就是豫道之至极,即是穷神知化。豫道是要求选择精义,能精一于义便能对将要发生之事处之泰然。精义入神是学者求圣之预备之道,在做事之前能精一于义,积累仁义,便在做事时有成就,能够精一地选择道义,就能物来顺应,非礼勿动,“‘精义入神’须从此去,豫则事无不备,备则用利,用利则身安。凡人应物无节,则往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养德也”。精义入神是圣人境界之前的预备阶段,遵守此豫道就会万事俱备,万事俱备就有便利功用,有利就会身安,就会顺应外在之变化,不执着于外物之牵累,这样就有利于存养内在道德。张载说:“大可为也,大而化不可为也,在熟而已。”“盖大则犹可勉而至,大而化则必熟。”大人境界是精义入神之有为有意之境,依靠主观努力可以达成;“大而化”的圣人是穷神知化之无为无意之境,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诚道,无需勤勉,自然与天地同流。故穷神知化是天人和谐的状态,是“诚于中,形于外”的内外自足、率性而为之境。
入神能够致用是因为神本身包含万物之理,通过精义进入神之境,就能对天下义理融会贯通,利用此义理便能开物成务,安稳生活,即“贯穿天下义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张载说:“穷神是穷尽其神也,入神是仅能入于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义固有浅深。”入神是神化的初级阶段,是初步地由外入内,由浅入深;穷神是穷尽神之妙道,彻底达到了与神化合一的状态。入神是穷神的路径,精义又是入神的前提,精义即是穷理尽性,如朱伯崑说:“义理有深浅,穷理到其精深之处,即是精义。”精义是穷理的精深之表现,精益求精地穷理就能穷尽到事物之本性,进而知晓气化之规律,此即可入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须以精义为前提条件,知性命本质上就是知气化,“因为人和万物的性和命皆气化之产物,不认识气化的规律,谈不上懂得性和命”。性命的本质都是气化,知理知性就在于知气之神化。张载说:“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知天知人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同意。”知天知人即是穷理尽性,穷理是将天理认识到最大化,进而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本性,如此变便通向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要经过“入神”和“存神”的过程,精义是充分地思考仁义,主动发挥天生的思虑能力去察伦明物,以深入觉知道德义理,充分认识事物本质,此即“入神”,进而体悟到气之神化,直觉到太虚之境,此即“存神”。从“入神”到“存神”即是从知觉到直觉,存神无须思虑,是消解了主观的天人合一之境,“是人的精神与天为一的状态,即完全与天地之化同流,顺乎阴阳二气变易的自然法则,已不为个体事物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利害得失所牵累”。因此,穷理尽性需要精觉明察的道德认识,勿忘勿助的道德体悟,经过此入神、存神之路进而能穷神。
(二)存神即是穷神
精义入神、利用安身是有为之境;穷神知化是无为之境,是自然圆满的超越境界。崇德和盛德分别是入神和穷神的核心内涵,向世陵说:“‘精义入神’、‘利用安身’作为大人的事业是可为者,而且应当是竭力推进……至于能否达到‘德盛仁熟’的最后境界,则不是主观强求所能奏效。它是水到渠成式的自然圆满。”精义入神、利用安身是困知勉行、学知利行的阶段,须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神。穷神知化是圆满成熟、无意无为的圣人境界,表现为从心所欲,物我两忘,无修无为。大人是自觉之境界,圣人是自由、自然之境界。同时,常人、大人和圣人三者不是割裂的,常人通过努力崇德和致用会成为大人,大人继续精义、安身,有勿忘无助、顺其自然之心态,便可进入德盛境界。朱伯崑解释:“精义入神是存神的条件。”入神和存神是穷神知化的两个阶段,分别取自“精义入神”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入神是穷神的条件,存神是穷神的方式,君子惟精惟一地践行仁义之道,最终自然能达到与神合一。
张载说:“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存神是无思无为,合于自然;顺化是勿忘勿助,顺应变化。张岱年说:“存即存之于心,亦即直觉之意。对于神,不可用思虑,唯当用直觉。对物之直觉,谓之‘体’;对神之直觉,谓之‘存’。所谓穷神,亦即由‘存’而穷之。”神不可用理智来思虑,不可用知识去表达,故靠直觉。直觉神化即存神,穷神所依靠的方式是存神,而非知神。张载说:“无我然后得正己之尽,存神然后妙应物之感。‘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过则溺于空,沦于静,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存神与无我相关联,无我即是无私我,如此能正己、安身,“以自己的生命为气化的产物,不以身心为个人所私有”,能真切体悟到神就能感物而动,与事物产生默契之感应,既能顺应天地阴阳之气化,不执著于一己之私,又不会蹈空于天地之外,沉溺于虚空之境。张载说:“‘精义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尝不接物。”精义入神是接物而不执著于物的道德境界,而不是脱离事物之空静。存神虽可以说是直觉,但这是有前提的直觉,不是无任何修为的当下即是,如朱伯崑说:“张载以存神为最高境界,其存神说,并非提倡直觉主义,而是以精义入神为前提的。”“精义入神,利用安身,乃崇德的前提,但只停留在精义入神上,反而不能达到存神的境界。”故存神以入神为前提和基础,需要认识道德、修养道德、直觉体悟等方式共同达成,但它又是对入神的超越,此超越即表现为不加勤勉,无须智力和思虑。因为思虑是主观的,存神是需要消解主观以与客观合一的神化之天道,“此种合一说,就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说,表面上主张虚心以接物而无所系着,破除憧憧往来之心,实际上将主观融化于客观之中,陷入了自然顺化论”。这说明张载的神化论受到了魏晋玄学之易学的影响,但张载又批判佛教追求空寂,不知气化之本质,否定现实的流弊。他主张穷神知化是为了使人们不被神化之外的糟粕所牵累,但又不会厌恶气化之生命,因为神化即在气化之中。张载教人不执着于外物,是因为外物皆因气化而变动不居,但外物之变动不代表万物是虚幻,气化皆是实有,自身与万物皆在宇宙之大化流行之中。存神即是与宇宙万物复归于气化之统一体。因此,如朱伯崑说:“张载的穷神知化说,虽然受了玄学派易学的某种影响,但他坚定地反对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进而批判了佛道二教的生死观。”故其为反对佛道之虚无提供了有力武器。
三、自信而自由:神化论视域下的圣人境界
张载说:“大而位天德,然后能穷神知化。”孟子说:“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人位居天德,能保存天地之神,顺应万物变化,“‘穷神知化’,与天为一,岂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尔”。穷神知化就是要不断破除自我,以达到与天为一体,即“无我而后大”。无我就是克服心之牵累,人与天本为一,因有我而分开,盛德就是复归于物我两忘之境。神为圣,又是不可知之境。张载说:“圣位天德不可致知谓神。故神也者,圣而不可知。”“圣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不可知”可理解为不可为知识,神不可用科学、理性的知识来认识。神化之境是一种需要体证、直觉的精神境界,穷神知化就是达到了主客统一、物我不分之境,如冯友兰说:“这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经验,一种体会,严格地说,不是一种知识。有知识就有所知的对象,这就有主观和客观的对立。而‘穷理’的目的,正是要‘合内外’,取消这种对立。所以‘穷理’的成功,就是这种知识的消失。”张载的修养功夫是以民胞物与、万物一体思想为本体论依据,人们通过积善成德可以穷神知化正是因为天人本为一体,人之本体即在神化之中,“‘化’、‘神’也都是宇宙的‘化’、‘神’,所以穷神知化,不仅是求知,且还是穷宇宙未竟之功,这是《西铭》之高深所在。”穷神知化即是要达到宇宙终极、究竟之境界。神化论彰显了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自信,神和化虽然是天之能,但人在其面前不是卑微的,完全可以通过主动地崇德广业来穷尽神化之道,从这个角度来讲,人能够与天地并列,因此,“正是基于人充分发挥其认知能力而可以‘极深而研几’乃至‘穷神知化’的理性自觉和理论自信,《易传》作者通过其系统性的道思维而提出了一种兼综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世界观认知模式”。这与《中庸》中所说的通过至诚来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至诚之道即是神的体现,能穷神知化就能赞天地之化育。
穷神知化表现为圣人的无为而治,是“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犹大而化之”。人对神的认知即是道德内化的过程,入神是道德内化的开始,穷神是道德内化的终点。穷神知化是知行统一、心天合一的完全自然的内在超越之境,并不是单纯依靠“时时勤拂拭”的刻意练习就能实现的。此境界需要“实践-认识-实践”地不断循环过程,将作为知行本体的良知完全呈现,“使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等完全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品质,使道德行为完全成为了一种高度的自觉、自主和自然行为”。经过不断尽心、知性、知天,不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久而久之对道德的认识和实践能熟能生巧,出神入化,使得心之德变化日新,圆满成熟,最终达到心与天合。所谓心与天合,即是将天之神转化为心之德,也是将人的道德性命升华为太虚之神。从这个角度讲,这种“盛德自致”的神化状态类似于认知心理学上的心理表征,它是经过长期地刻意练习之后建立的心理结构。张载还有很多关于“穷神不思不勉”的说法,比如:“以理计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则无修。”“盖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则不可加功,加功则是助长也,要在乎仁熟而已。”故穷神知化是破除见闻之狭的无偏无私,克服“意、必、固、我”的束缚,而达到的从容中道、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此即与气化同流之境。张载说:“义有精粗,穷理则至于精义,若尽性则即是入神,盖惟一故神。通天下为一物,在己惟是要 ‘精义入神’。”穷理至精益求精处即是精义,精义便能尽性,尽性到至诚境界即是入神。神是一,即“与天为一”、“通天下为一物”。达到神之大一的状态就能物来顺应,无滞无着。穷尽神化即是养成盛大之天德,故君子通过崇德就可以穷神,无须走佛老之路。礼乐之德是通向神化的必由之路。穷理即是实实在在地穷究儒家之义理。张岱年说:“穷神知化,在于无我而与天为一,即在于广大的直觉。此种直觉,基于道德的修养。张子最注重道德修养与致知的关系,以为知道之道在于崇德,德盛则自然能穷神知化了。”通过道德修养,获得德性之知,就能穷神知化。能穷神就能穷尽天地万物之性,就能意识到人与万物统一于一个总体的性,就能超越个体之私,返归于神化之大公。大人能兼爱万物,因为大人意识到万物皆是气化,人之性与物之性同根同源。
精义入神要通过仁义达到,如张载说:“义入神,动一静也;仁敦化,静一动也。仁敦化则无体,义入神则无方。”神与化分别对应义与仁、静与动。由义进入神,是由动进入静,由有思有为之精义达到无思无为之神;由仁达到敦化,是由静入于动,由无思无为之神开展出百思百虑之过程。神化是动静结合之境。气之神妙变化生生不息,蕴含化育万物的生生之理,此即仁义之表现。穷神通过义,知化通过仁,仁义推扩到极致就是德盛境界,圣人就是此“仁至义尽”的神化之境。张载说:“德盛者,穷神则知不足道,知化则义不足云。”智是神之高明智慧,义是化之适宜性,将智和义推至其极就可通向神化,而一旦能穷神知化就会超越智、义而达到盛德。德盛仁熟的圣人达到了至高的中庸之道,如张载赞美孔子说:“仲尼应问,虽叩两端而竭,然言必因人为变化。所贵乎圣人之词者,以其知变化也。”他又评价颜回说:“盛德之士,然后知化,如颜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尝不知’,已得善者,辨善与不善也。《易》曰‘有不善未尝不知’,颜子所谓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处便为不善而知之,此知几也,于圣人则无之矣。”这是说,颜回能在有形有迹的地方发现不善而立马改正,差不多达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的知几境界,但尚未完全能通向无形无迹之神化之境,未能完全体悟无形之变化而获得从心所欲之自由。
四、结语
张载认为,神化为主体,宇宙之其他皆是客体,神化贯通一切,“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杨立华解释:“张载突显了神化的至真至精。而正是至真至精的神与化,才使得法象、形性不至沦为构成宇宙的“质料性”的存在……没有看到贯穿其间的神化作用,那么,即使性与象这一层面的形上者,也会沦为僵死粗质的糟粕。”此神化论推之于人道即是,人意识到万物与自身本质为一,故要在精神上不留滞于法象,与宇宙之气化融为一体,关切万物即是关切自身,自身之成德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人之本质不在于法象而在神化,故不应执着于暂时的物质生命,而应精义、入神、存神、穷神,以获得永恒的道德生命。但是,“法象皆是糟粕”并不代表“法象皆是空无”。穷神知化是道德盛大之境,不是佛老之无道德的虚空境界,穷神知化与仁义礼乐相统一,此即上达与下学的结合。穷神知化所要求的具体事务是“知义用利”、进德修业之事,这鲜明地体现了神化在儒家中的入世特质。如张载说:“世人取释氏销碍入空,学者舍恶趋善以为化,此直可为始学遣累者薄乎云尔,岂天道神化所同语也哉!”神化不是空无,不离仁义。王夫之在《正蒙注》中说:“张子推天道人性变化之极而归之于正经,则穷神知化,要以反求大正之中道,此由博反约之实学。”穷神知化是由博返约,通过六经之德目复归于神化之中道。王夫之也评价张载《乾称篇》说:“补天人相继之理,以孝道尽穷神知化之致,使学者不舍闺庭之爱敬,而尽致中和以位天地、育万物之大用,诚本理之至一者以立言,而辟佛、老之邪迷,挽人心之横流,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儒家之穷神知化不离孝悌伦理,以人伦日用中的爱敬之情为实现途径。佛教思想与张载的神化思想有根本区别,神蕴含天地之实性,气化之万物也不是真如的障碍,而是神之流行发用。神化的“不可知”须从日常伦理的“可知”来达成,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程颐也认为神化之境不能脱离人伦庶物:“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释道所见偏,非不穷深极微也,至穷神知化,则不得与矣。”这既使得穷神知化有了落脚点,又使得礼乐获得了合法性、神圣性。
《系辞》作为《易传》义理之代表,所包括的“穷神知化”思想对发展儒家之道德性命学说有重大意义。如韦政通说:“照传统的说法,系辞是以‘穷神知化’的方式解易,高度发挥了哲学性的玄思。就哲学的观点看,系辞比其他各传更具哲学的价值。”“穷神知化”作为《系辞》的根本思想之一,经过张载的创造性阐发,成为宋明易学的重要理论。汉唐以来易学家都没有将神和化进行专门的义理化诠释,而张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区别入神和存神之序列,以后者为穷神之最高境界,并与《孟子》《中庸》思想相融合,对宋明解《系辞》有重大影响。神化论作为张载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总纲领,使得其哲学思想不仅仅停留在气的层面,这对深入研究太虚、太和思想提供了重要根据。张载的神化论对程朱理学以天理为核心的本体论建构有重要启发,也深刻影响了王船山的神化思想。研究张载的神化论,对《周易》心性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有重要作用,也对现代道德修养、精神信仰、天人合一等论题有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冀公网安备13010502001495号 网络维护:齐战强
冀公网安备13010502001495号 网络维护:齐战强